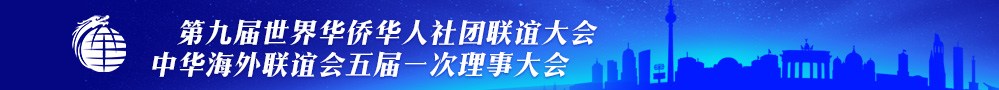保罗·克利(Paul Klee, 1879-1940)
对疾病与死亡的描述是克利艺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经历了病痛的折磨之后,他的作品不仅在主题上呈现出关于人生悲喜剧的深度思考,在形式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作品的象征性加强了,构图也更加自由,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正像格罗曼所说,克利生命的最后三年半时间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时期。本书认为,克利作品形式的改变来源于疾病对艺术家身体的影响,对身体的感知和体验影响了克利关于生成的态度,决定了克利从一个更高的哲学视角去看待生命同死亡之间的关系。自然的真理在克利的中间世界显现,这是一种在现世中找到自己的居所、细心培植自我的真理。
保罗·克利《病中女孩》1937

保罗·克利《花女》1940
在这些画作中,克利不纯粹是对悲剧人物进行描绘,而是从根本上去思考人生的有限性与命运问题。自被驱逐出德国以来,克利的作品多多少少展现了悲剧的色彩,如《悲伤》《毁坏的村落》《破碎的钥匙》等。随着其患上不治之症,克利关于航行的画作越来越多,如《船上的病人》《黑暗旅行》等,这些关于渡船、旅行的题材就像描绘生命的历程中那种种的不安。
保罗·克利《破碎的钥匙》1938

保罗·克利《黑暗旅行》1940
在传统意义上,悲剧割裂了世界。与变动不居的现实命运相比,人们总是被引导去相信还有一个充满着和谐的永恒世界,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基督教的天国等。悲剧中的一面是静止、一面是运动,两者此起彼伏的斗争造就了悲剧。但是,克利并不赞同这种普遍意义上的悲剧,从他对浮士德的反对就可以看出: 浮士德的悲剧根源于其内在的冲动与外在的限制,他原本只在书斋里享受着世界的宁静,这同他内心深处的冲动形成对比。魔鬼引诱浮士德时,许诺他可以经历世界上一切的感性体验,这就是浮士德最终酿成悲剧的原因。与浮士德追求永恒的享乐而不得的悲剧相比,克利选择同一切静止的事物保持距离,这也是他同好友马尔克相区别的原因。实际上对于克利来说,真正的悲剧不是追求静止而不得,而是有限性阻止了对思想的运动。正如前文提到的,克利从“箭头”中就已经看到,人这种不时产生的希望与其自身局限性之间的对比是所有人类悲剧之所在。
保罗·克利《船首的英雄式划桨》1938

保罗·克利《计划》1938
克利对悲剧的体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构图和形式,格罗曼将其最后时期的作品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嵌在明亮的树胶水彩上的象征符号,第二类是像条带一样大且厚重的黑色象征符号,第三类是色彩明亮、光环状的象征符号。不同种类的象征符号所传达的气氛也同题材指向一致,如《恐怖的信号》(1938)的总体基调就十分忧郁,此时克利不知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德国土地上那残酷的杀戮和扭曲的社会状态。
保罗·克利《恐怖的信号》(1938)
而同时,尼采所说的那种悲剧精神此时也以一种张狂和激烈的力量显示在克利的作品中,无论是线条还是色彩都不再保持过去的细致和敏锐,而是展示出一种粗放的气质。在象征悲剧的狄奥尼索斯那里,“酒神的激情就苏醒了,随着这激情的高涨,主观逐渐化人浑然忘我之境”,再加上克利最后时期倾向于创造大尺寸的画作,这也使得他的绘画同利奥塔笔下的纽曼、埃尔金斯笔下的罗斯科的作品一样成为欲望的原初表现,画作的基调和用色更容易从情感上感染观者。例如《B近郊的公园》(1938)中对色彩的使用并不讲究章法,只是在界限处给予提示,这种描绘甚至让人想起马蒂斯成熟期的作品。
保罗·克利《一个无足轻重却自命不凡的家伙》(1927)
这种变形带来的幽默感与讽刺力量总是从克利的作品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如《一个无足轻重却自命不凡的家伙》(1927)中,人物的性格从线条结构(紧闭的双眼、零落的头发、狭长的面部)中展示出来;《最后一个唯利是图者》(1931)中扑克牌似的形象展现了一个狡诈的人物,他翘起的胡子、微笑的嘴唇与不自觉伸出的手都展现了其品格。施马伦巴赫感叹道,克利将所有艺术的严肃转成自由的表演,为了对抗这种严肃,他不惜受他的无休止的幽默所主宰。
保罗·克利《独翅英雄》1905
克利在早年的绘画作品中多次刻画了他所谓的悲喜剧人物,例如前文提到的《独翅英雄》。这一追求自由精神的形象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而导致了悲剧,但其形象的细微之处可见幽默因素(僵硬的姿势与表情,脚上长出的植物)。克利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悲喜剧的英雄,也许是一位古代的堂吉诃德。还有《老凤凰》(1905)中那个拿着权杖的年迈凤凰,克利认为其不是什么理想人物。活了五百年之后历尽沧桑的模样和寓言造成了喜剧效果,但“凤凰不久即将退化成单性生殖动物”,这一观点中也透出小小的幽默。而观者见到这一失去了荣光和羽毛的形象之后,这个人物还昂着头、保存着仅有的尊严,心中所向往的理想与现实形成对比的悲剧感油然而生。
保罗·克利《老凤凰》1905
为了避免悲剧带来的对世界的虚无主义,同喜剧带来的过度娱乐化,我们应当住在中间世界,并且取得人生的平衡。克利的这种观点在晚期作品《甘苦岛》中显现出来。
保罗·克利《甘苦岛》1938
《甘苦岛》是克利最大的一幅画(88×176cm),它是将报纸平铺在麻布上作为底子画上油彩而成,报纸被吸收进织物中,从画作表面可见其纹理,作品主题是克利拼贴而成的短语“Insula Dulcamara”: 甘(dulcis)与苦(amarus)被合并成为一个中间词汇——甘苦。同时,这个词还让人联想到当时欧洲的一种致命植物“Solanum dulcamara”,即小颠茄,这是含有神经性毒素的一种常见植物,看上去甜美,但过度食取便会致命。这幅画的色调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代表生机的黄绿色和玫瑰粉铺满了整个画面,鲜红点缀其中,黑色的海岸线衬着航行的轮船,沉没的落日是黑色的半圆、升起的透明半圆是初升的太阳。这是克利第一次尝试大尺寸和新材料的作品,也是刚刚战胜了病魔的克利对人生的真诚感悟。人生就像这甘苦之岛,充满着各种不同的际遇,但能肯定的是一切都会隐隐之中达到平衡: 如果甜美过多,苦难也就过多,保持生之平衡就是在人生的馈赠中拿取同等程度的甘苦。
《使不可见者可见——保罗·克利艺术研究》苏梦熙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