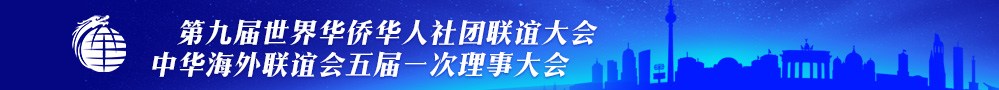我们怎么定义网红?它是超越时间,超越地理,超越线性认知范围的流行,突兀与迅速是红的重要美学部分,而批量复制则是毫无商量余地的结果。也因此,无论这个时代的人自身还残存哪一点年代感与地域感,无论你从Instagram还是小红书上观看世界,文化隔阂已被攻克,消费形式(此处包括教育消费)取代认知过程,一不小心,曾经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头被迅速祛魅,成为打卡自我的背景。
我们怎么定义网红?它是超越时间,超越地理,超越线性认知范围的流行,突兀与迅速是红的重要美学部分,而批量复制则是毫无商量余地的结果。也因此,无论这个时代的人自身还残存哪一点年代感与地域感,无论你从Instagram还是小红书上观看世界,文化隔阂已被攻克,消费形式(此处包括教育消费)取代认知过程,一不小心,曾经令人望而生畏的山头被迅速祛魅,成为打卡自我的背景。 在这个后当代的岛屿,花鸟岛国际动画艺术节主办方和一众80、90后年轻艺术家操办了一场与这岛屿有关又无关的展览。网红旅游业早就做好了花最少的时间直奔先锋的准备。位于花鸟岛游客中心的展览空间底楼平时主要卖摆渡车票,大堂门口“禁止吸烟”牌子边上有面正方形的镜子,上面赫然用灯管写着一句歪歪扭扭的英语——“Where am I from”。这恐怕不是当代艺术,而是批量复制的后当代淘宝网红装饰艺术。对不起,我很难否认其具备某种极简主义美学里难以复制的东西。
在这个后当代的岛屿,花鸟岛国际动画艺术节主办方和一众80、90后年轻艺术家操办了一场与这岛屿有关又无关的展览。网红旅游业早就做好了花最少的时间直奔先锋的准备。位于花鸟岛游客中心的展览空间底楼平时主要卖摆渡车票,大堂门口“禁止吸烟”牌子边上有面正方形的镜子,上面赫然用灯管写着一句歪歪扭扭的英语——“Where am I from”。这恐怕不是当代艺术,而是批量复制的后当代淘宝网红装饰艺术。对不起,我很难否认其具备某种极简主义美学里难以复制的东西。 曹澍的作品还是当代作品,李昂的作品接近后当代的作品。情绪是真诚的,表达是直接的,且我们用来理解这一切的头脑,我自知,已经脱离当代艺术的逻辑。很难说大多受了西方当代艺术教育的80、90后中国艺术家是否有意与吞吐苦难符号的前辈们一刀两断。如我之前所说,后当代的世界是不讲先来后到,更是不讲所谓的艺术史的。卢川、杜晨艳策展的主展览环节和杨静策展的游戏环节都与数字媒体打交道。他们的焦虑与物质生活毫无关系,被媒介裹挟与用相同的媒介破除裹挟是无法破解的二律背反。但我们能体会到这种被困感,因为这正是我们来花鸟岛试图逃离的东西。李亭葳的《数码手指》把“手机”里的“手”与“机”分解开来,用3D模型做出了一只空空如也的手,并用更多的数码影像追踪这只手。我们面对这空对空的荒诞,心里是种什么滋味?是更看得起自己的手,还是更瞧不起手机?费亦宁的《三个翅膀》困顿感更强,仿佛灵魂也被数码(艺术)困了进去。影像中女声不断重复:“it's okay”——但真的okay吗?阳芷倩的《起飞点》是个元二次元叙事——虚拟人物被困于虚拟世界,出不来,那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最后要提到大悲宇宙&李晓岚,数码艺术家与花艺师合作的作品《数据合成昆虫-虚拟蝴蝶》,花是真的,蝴蝶是假的,说实话没哪里违和,在保证插电的情况下,相处十分融洽。我们讨论了很多年艺术与新媒体的关系,最不敢谈的是今天的数码艺术终于有了艺术本该有的装饰功能,并在这条道路上前途无量。
曹澍的作品还是当代作品,李昂的作品接近后当代的作品。情绪是真诚的,表达是直接的,且我们用来理解这一切的头脑,我自知,已经脱离当代艺术的逻辑。很难说大多受了西方当代艺术教育的80、90后中国艺术家是否有意与吞吐苦难符号的前辈们一刀两断。如我之前所说,后当代的世界是不讲先来后到,更是不讲所谓的艺术史的。卢川、杜晨艳策展的主展览环节和杨静策展的游戏环节都与数字媒体打交道。他们的焦虑与物质生活毫无关系,被媒介裹挟与用相同的媒介破除裹挟是无法破解的二律背反。但我们能体会到这种被困感,因为这正是我们来花鸟岛试图逃离的东西。李亭葳的《数码手指》把“手机”里的“手”与“机”分解开来,用3D模型做出了一只空空如也的手,并用更多的数码影像追踪这只手。我们面对这空对空的荒诞,心里是种什么滋味?是更看得起自己的手,还是更瞧不起手机?费亦宁的《三个翅膀》困顿感更强,仿佛灵魂也被数码(艺术)困了进去。影像中女声不断重复:“it's okay”——但真的okay吗?阳芷倩的《起飞点》是个元二次元叙事——虚拟人物被困于虚拟世界,出不来,那好像是理所应当的。最后要提到大悲宇宙&李晓岚,数码艺术家与花艺师合作的作品《数据合成昆虫-虚拟蝴蝶》,花是真的,蝴蝶是假的,说实话没哪里违和,在保证插电的情况下,相处十分融洽。我们讨论了很多年艺术与新媒体的关系,最不敢谈的是今天的数码艺术终于有了艺术本该有的装饰功能,并在这条道路上前途无量。